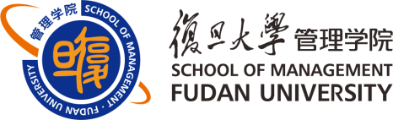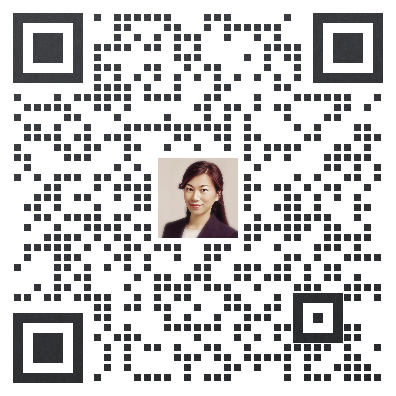瞭望东方周刊—陆雄文院长专访:上海“怎么办”


身为经济学家,与企业家打交道极多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还是大段大段地谈到了改革这个政治性话题。谈及上海的改革现状,他觉得“改革豁免令”既值得高兴,又有些无奈。这一矛盾的态度,投射出当下改革的复杂现状。上海遇到了什么问题,上海应该怎么办?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评价上海出台的改革豁免条例?
陆雄文:上海出台这样一个决定,为什么引起比较大的反响,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体制变得更加固化和僵硬。尽管我们一再提改革,但是过去十多年来,改革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这也是再一次呼应了中央领导对于改革是最大红利的重要观点。因此上海出台这个政策引起大家的关注,我觉得这是积极的方面。
但是回过头来想,这是蛮可悲的。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改革创新都是有风险的,改革创新有风险,意味着就一定会有挫折和失败,意味着必须应该有宽容,应该让改革失败的教训成为公众的财富,来警示后来人绕过艰难险阻,用更好的方法去克服困难,然后找到发展的道路。但是今天却用这样的方法在政治上来保护改革,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悲哀,一种无可奈何。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发展受阻的原因是什么?
陆雄文:上海的国有企业曾经是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企业。但是,过去30年上海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挣扎在夹缝中。对外来讲,它们面临开放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对内来讲,是来自央企、民企的挑战。上海那么多辉煌的品牌,一个个都倒下了,这跟上海现在的经济地位、商业历史、优秀的人才素质是相悖的。为什么?因为从体制上来讲,我们约束了上海发展一批真正的企业家。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受体制的束缚,他们对政府组织部门负责,通过干部的筛选机制来筛选,而这种筛选的标准主要是在政治上合格。这种背景决定了他们首先必须服从政治正确的指引,在市场中迎接挑战就成为一个次要目标。所以过去30年里,我们的国有企业在这个体制的温水的蒸煮下,像青蛙一样慢慢的失去了知觉,丧失了改革的动力和勇气。
发展企业有很多方面需要突破,这些突破不是三年五年,要很长时间去部署,但是企业领导知道这样的部署毫无意义,因为他可能被随时调离。国资委的考量都是每年以资产收益率、产值、收益或者利润的指标来完成的,所有的企业都变成了短期的驱动。在制度上,我们对官员,包括对国有企业领导的要求变得不容许你犯错。比如国有企业的考核,每年都要有资产收益率高于平均水平,每年的利税都要比去年有增长,这是最违反经济规律的。宏观的经济有周期,行业产业发展有波动,对于每个企业,它不可能在一条直线上保持一定斜率的增长,所以国资委的要求本身就违反经济规律。
如果说上海有一点成功的企业,那是两类:一类像上海汽车这种企业,它不是完全由企业家的自主变革创新为驱动力,而是一种环境、政策来托底,抬起这个企业的规模和收益,另外一类企业就是振华港机这样的企业,央企,不受地方政府的主导。振华港机曾经一度的辉煌就证明了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对于企业的重要作用,像管彤贤这样的企业家,他忘掉了自己的政府背景和自己作为央企官员的角色,完全站在市场的角度,前瞻性地看待企业的未来,愿意去承担风险去变革。
所以今天我说最现实的改革是有两个:第一,在经济上重塑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打破政府对于国有企业以所有者名义去全面掌控主导企业的行为,国有企业改革讲了30年,首先提的就是政企分离,到现在还没做到;第二,充分的法治环境。我们法律现在不是制度问题,是执行问题,通过有效实施来保证自由经济和公平竞争,我们还没有做到。如果这两点做到了,资源配置就会优化,竞争变得有效,企业就变得更加有竞争力。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一直是企业家辈出的地方,现在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的企业的发展,从历史渊源上来讲都是受上海的影响。除了国有企业的体制原因,如何看待上海民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与多数人生活息息相关的IT产业,相比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上海没有自己的领军企业。
陆雄文:我们今天面临未来的道路,不是简单重复的原来的历史或者别人走过的路径。比如说为什么马云在杭州创业,这没有先例可以来遵循,其实到哪里都无所谓的,只要有些条件,比如说有人才,这些人并不是最高端的技术人才,杭州就有大学,够支撑了,但不能跑到贵阳或者到乌鲁木齐去。包括腾讯,在二线城市中创业,成本低,资源可获得。
为什么上海过去十几年民营企业发展不利?因为国企和外资强大,造成上海商业成本很高。比如十年前,我做职业经理人,到外资企业去工作一年10万年薪,到创业企业1年拿2万,如果失败了,还要再回到外资企业去,重新爬楼梯。能不能再持续创业?没有这个环境。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创业资本供给不充分。现在有大量的PE和VC,我觉得这个是机会。
今天上海的创业成本仍然比别的城市要高,所以这里只能适合高技术人员,就是说我到上海创业,我不能只拿2万。到外资企业我去打工做经理可能拿10万、20万,我在创业企业一年可能拿7、8万,然后我拿股权,那我还玩一把。你如果再给我2万就不干了,在西部现在还可以这么做,在上海不行,上海只能走更加高端,更有附加价值,更有技术含量的创业道路。
当然,我们注意到逆向选择,即现在很多PE和VC,尤其是PE选择走传统产业,这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考验。如果不能迅速地把原来低知识密集的结构转向高知识密集的结构,为什么PE要去找这些低知识密集的呢?因为它风险小。当PE都不敢去承担风险去投入,那高科技的东西就无法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在上海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最引人瞩目的。如何看待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
陆雄文: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赖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是市场要开放。我们现在的市场还是封闭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构成了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客观的外部限制。最近我看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人民币可以同某些外币直接兑换,在海外设立了一些人民币结算中心,第二是容许境外投资者更多参与国内资本市场,包括港澳台的居民,但这仍然不构成一个充分的开放市场。当一个市场不能充分开放的时候,国际金融中心就无从谈起,充其量是本国的金融中心。
第二,不仅需要硬件基础设施,还需要软件的基础设施。比如我们的法律,中介机构,知识库或者数据库,这些建设都不足以让我们的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的能力都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相匹配。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我们产品的选项很有限,无论是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还有指数产品,以及对冲机制都非常有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开放的自由交易市场,必然充满了投机,所以对投机的预测和限制,以及对于利用制度和市场缺陷而产生的冲击和风险,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把控,在知识和能力积累上去把控,那我们开放也意味着灾难,这是对我们的法律和监管体制的要求,而这方面我们还缺乏一个成熟的体系。
第三是人才队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人才?一方面,上海号称有几十万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但另一方面又缺几十万的金融从业人员,为什么?拿金融学位的本科生、硕士生在上海集聚,为什么我们还去引进人才?原来我们学校的金融课程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衍生出来的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国际金融和一些宏观经济学的课程,甚至是从国家的宏观金融政策的选择上来进行知识体系的传授。但是,金融课程主要是培养资本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所以上海政府突然发现我们大学的体系跟国外完全不接轨。
所以我们还存在很多的困难,三个条件现在都没具备。上海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其他城市更是口号,因此绑架了很多资源。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你如何评价?
陆雄文:对于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提出很多口号,口号的色彩重于实质。比如上海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内地多个城市都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或者区域金融中心,这说明我们不知道中国需要多少个金融中心,以及如何才能建设金融中心,甚至不知道金融中心该是怎么样,经济上的目标成为了政治上的口号,这会让我们的资源错配,让本就比较稀缺的一些高端经济资源成为政治追求的附属品。
其实上海提出四个中心实在不够专业,为什么?经济、金融、航运、贸易四个中心,经济中心这个广义的概念一定覆盖了很多领域,金融、航运、贸易只是经济的一个部分,它们又有重合。金融、航运和贸易是跟上海的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和历史传统紧密相关的,而且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历史上,金融、航运、贸易都紧密相关,比如说纽约、东京、香港,乃至新加坡,一个城市成为航运中心,一定会有贸易,有贸易就有资金。无论是从历史、经济结构和地位、地理位置,上海都具备成为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条件。能不能成为综合的经济中心,那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应该把经济跟另外三个中心并列,这是最基本的专业判断。
今天这个目标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问题是对上海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样?我觉得,金融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我认为是高科技中心。因为有产业基础,我们把制造业完全扔掉是不可能的,但是制造业的大部分必须放弃掉,汽车、化工、钢材,长远都应该放弃掉,但是在医药、生物遗传工程、高分子材料方面,上海有很大优势,另外核心的还有IT。第三,我觉得上海要成为一个商业智慧中心,以此来调动产业发展,上海应该成为很多企业的总部中心,因此可以调动航运、物流、贸易。有了这三个中心,上海必然就是一个经济中心,航运、贸易都是延伸和附属,而不是追求的终极目标。现在我们拼命去建码头,去搞博览会,某种意义上来讲那是本末倒置。
《瞭望东方周刊》:这就回到前面你说的上海企业发展问题,也就是说上海的机会只可能在高端产业。
陆雄文:是的,但是上海有没有能力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个问题。而且,不光是意识到,也要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关键,就是要营造适宜高端产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
-

新闻动态
-

活动讲座
-

微信头条
-

招生咨询
-

媒体视角
-

瞰见云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