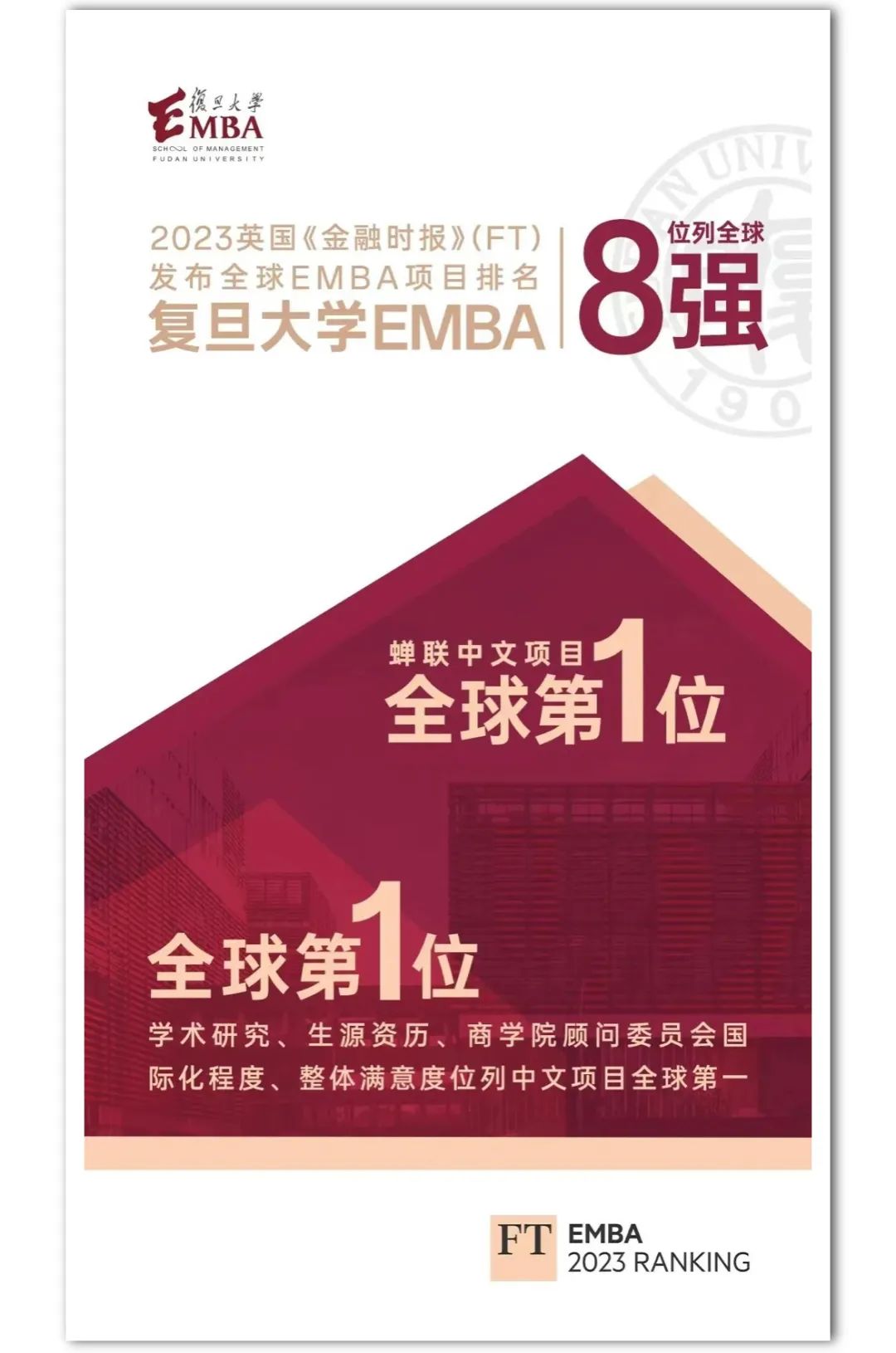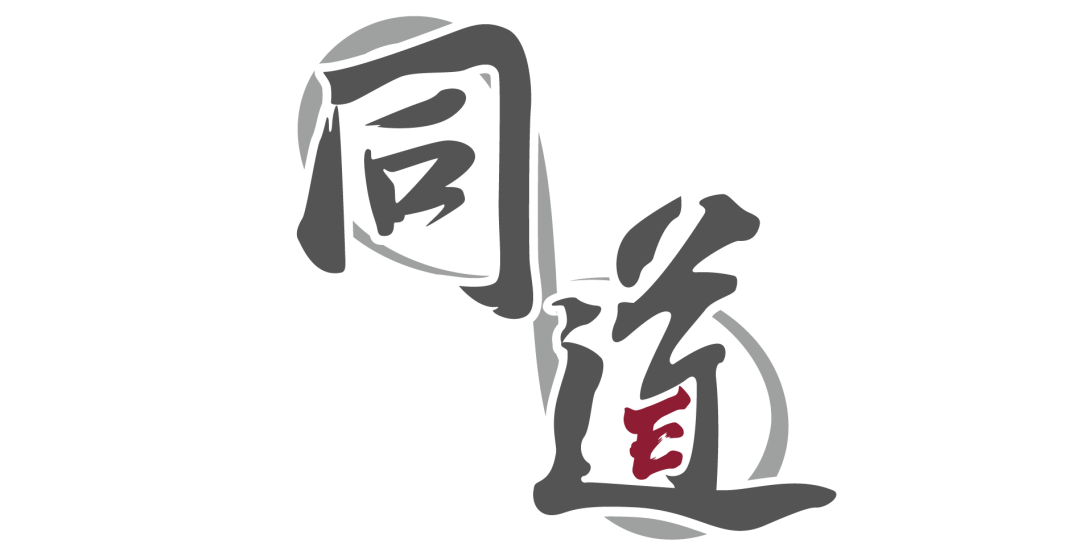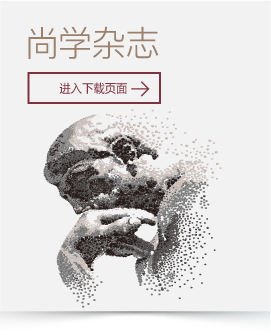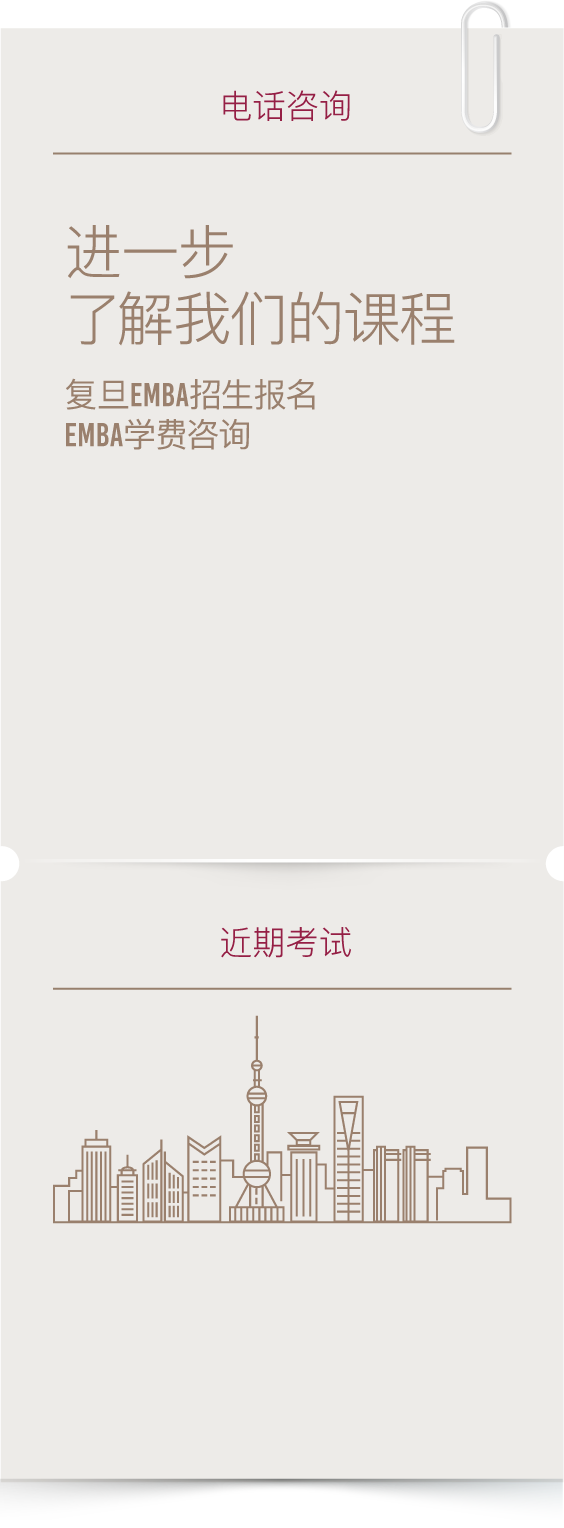校友 徐立勋
2002级复旦大学EMBA校友、复旦管院2018“年度校友”
现任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华茂集团第二代掌舵人
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拥有50年以上发展历史的可谓凤毛麟角。
华茂诞生于1971年,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经历过三次所有制改革。从宁波四明山上一家小小竹编厂,到中国最大的教育用品生产商;经过超过半个世纪、三代人的努力,从一个建立之初只为解决山里农户生计的小型加工厂,到如今发展成为集教育、文化艺术、科技、医疗、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回首往事,公司创始人徐万茂说:没有轰轰烈烈,只有踏踏实实;没有狂风暴雨,只有细水长流。而他唯一的儿子徐立勋,在不满三十岁接手家族企业的时候满怀压力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年龄还不如我所接手的企业大。”
在徐立勋看来,一个家族企业传承成功与否的关键点无非两个,即上一代愿不愿交、新一代能不能接。愿意交棒的,也不能仅是形式上的交权,因为只有虚衔没有实权的接班过程只会更加艰难。而二代三代是否有兴趣接班、是不是适合做企业,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每位家族企业继承人在接班时都无一幸免地面临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对担负重任的忧虑,更多来源于现实中发生的窘迫。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接班时的权威失落。心理压力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我父亲做得很成功,所以社会舆论理所当然认为我要做得比父亲更好。另外一个是大家庭里面的压力,我上面有三个姐姐,我父亲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家族内部也会给你很多压力。” 徐立勋说。他觉得要为所有站出来接班的二代们点赞——这是一个围城,里面的人未必那么快乐,“因为你们都不是当事人,无法去感同身受我们这些二代所背负的责任”。
与其他民企不同的是,徐万茂把企业管理权交给儿子徐立勋时,只有55岁,年富力强,远未到退休年龄。2000年,华茂集团面临的美国官司风波将其置于危机中,徐氏家族第二代徐立勋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不得已被推到风口浪尖。此时,公司内老臣众多,徐立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2年,徐立勋被任命为总裁,但只有1000万元以下的投资决策权;2006年,徐万茂将董事长办公室搬离集团总部;2008年,徐立勋获得法人签字权和5000万元以下的投资决策权。父子俩用了近9年时间完成职权交接,然后又用12年时间共同推动华茂落实长远发展战略。在这个传承过程中,华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两代共治”新模式。
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用徐立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华茂对我的成长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在2004年的时候,徐立勋很痛苦,觉得自己在华茂仍是一个“说了不算”的总裁,太煎熬了。大叔徐万平劝导他说:“你知道军队是怎么培养领导者的吗?就是给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种任务,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和职权,还有意志力和领导力。”在核心接班阶段,徐立勋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经历各种挑战和压力,最终确立了他在华茂的地位。这六年,徐立勋形容它是“地狱般的煎熬”。对此他也能理解,毕竟就像军人需要战功才能够晋升,“企业很现实,不会因为你是创始人的子女就听你的,必须拿出让他们信服的业绩出来”。
他的业绩靠的是自己的投资眼光,先是主导了公司入股宁波银行,成为并列第三大股东,并在2005年后抓住了股市大牛市,在2007年春夏之交从股市全身而退,使得当时主业陷入困局的公司扭亏为盈,徐立勋的投资利润占了当年集团总利润的80%。“奠定了基础,我就不急了,从此可以按照我的步骤、节奏来做事情了。”他回忆说。
在徐立勋眼中,近10年来,中国民企出现了普遍性的“家族企业交班难”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源于接班人和父母在生活上的疏离。在家族文化上缺乏传承,又缺乏其他家族长辈的行为示范,最终导致家族的两代领导者不能在文化上“同频共振”,也就无法顺利完成交接班。
很多接班人的家庭教育出了问题,《红楼梦》中贾府的继承人贾宝玉接班就是他心目中典型的失败案例。曾经的徐立勋见到老爸能躲则躲,少年时就去外面住校读书了。他的叛逆期漫长,因为自己的每一个轨迹都是父亲一手安排的,故而更加抵触,充满傲气,脾气大、说话难听。
他观察到富二代成长过程中的缺憾往往发生在青春叛逆期,这一阶段他们特别需要父母的陪伴,偏偏父母处于艰苦的创业期,不能陪伴他们。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儿子徐钰程的出生才开始悄然转变。“我第一眼看到他,一下子感受到了责任的分量,瞬间从一个大男孩变身成了一个老父亲。”
徐家的第三代徐钰程是徐立勋的长子,正在纽约大学攻读计算机、经济学和艺术史三个学位。“徐钰程还小的时候,爷爷在书房里摊开一幅画,能和孙子两个嘀嘀咕咕讨论很久。在徐家,徐钰程是唯一一个可以从小在爷爷收藏的美术作品上赤脚行走的人,他对艺术的兴趣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徐立勋这样介绍自己的儿子。
基于对徐立勋成长过程中曾缺少父亲陪伴的思考,徐万茂和徐立勋在徐钰程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他的不是一种“控制型的优待”,而是一种“服务型的尊重”。徐万茂觉得孙子主要的挑战反而是责任意识过重了,由于太好强,给了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充分尊重他的选择,从不帮他做决定,但他来询问我时,我会给他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吸收了我和我爸在父子互动方面的教训。” 徐立勋总结说。
从儿子小学四年级开始,徐立勋每年春节和秋季都会专门抽空,单独陪儿子去参与一项公益活动,再一起参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徐钰程长大了之后,爷爷徐万茂又开始利用暑假陪孙子去国外看博物馆和美术馆。
徐家的教育理念是,价值观的树立是最难也是最关键的。因为价值观基础从小打得好,在徐立勋看来,儿子成长为一个“心态开放、阳光、正直的年轻人,而且很谦虚,所以长辈们都喜欢他”。他表示儿子大学毕业后会给他10年时间发现和尝试,“但10年后必须回来接班”。

徐家三代人徐万茂、徐立勋和徐钰程在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
徐万茂曾说:“前辈的所作所为不应该成为子孙成长的包袱。” 这位集团第一代希望自己给家族留下的是一根空心的竹子,留下事业,而不是财富。“我不想让我创造的企业给儿女们带来祸患,成为他们的包袱。我想确保徐氏家族凝聚一代又一代成员的努力,实现百年华茂的目标。”
徐立勋觉得父亲拟订《徐氏家族共同协议》的出发点很简单,不希望家族成员未来因为分割家产弄得六亲不认,也不希望华茂由于被后代分割股权而传不过三代。
经过长期的策划与准备,2008年8月,徐氏家族三代20多口人在《徐氏家族共同协议》上郑重签字。为了这个协议的搭建,徐家还聘请了一位美国律师和一位中国香港律师,同时聘请了一位中国传统文化专家。他们希望这个协议最终既能借鉴西方家族管理中先进的管理方式,又能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文化积淀。
《徐氏家族共同协议》主要包括三条原则,被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民营企业家族传承领域开了先河,具有示范作用。
首先是分产不分家 ,会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后成立家族信托,徐万茂会将其持有的77.83%的华茂股份永久性转移到家族信托基金,家族只拥有资产的保管权、经营权和红利分配权,没有所有权,家族企业永远不会在遗产继承过程中被子孙分割掉。
其次就是继承人的问题。协议很明确规定了长子、长孙这样的一个继承规则,遵循中国传统,但是同时会设置监督人的相应规则,如果继承人不合格的话有流程去罢免之。
基金会还会对所有家庭成员开放教育基金,但同时公司管理层不安排“皇亲国戚”入职,制度大于总裁和血缘关系,保证现代企业独立的管理体系和流程。
最后,一旦华茂经营不善进入破产程序,要优先用结余资产保住学校。所有结余资产都归学校所有,对教育事业承担无限责任。如果企业遇到不可抗力,徐氏家族将把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转移给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以表示徐氏家族对教育的最后贡献。
一个家族对于财富的态度代表着家族的荣誉观。《徐氏家族共同协议》体现了徐万茂和徐立勋两代民营企业家的财富观念和家族价值宣言,以教育家的心态规划百年传承大计,他们希望将这份事业流传下去。
对于将来,徐家想得很长远。
“
在徐立勋心目中,家族企业最大的优势包括规划的长期主义、强力的控制执行力和家族精神价值观的确立。“家族企业坚持的方向很重要,包括你追求的目标是眼前的还是长远的,不能以一城一池的得失作为家族企业评判的标准,家族企业对抗时间的韧性会比较足。”
家族企业在转型和创新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华茂每10年都会做一轮大的企业战略的调整,反思沉淀两三年,走向新的转型。同时,每10年华茂也会进行一轮管理上的变革、组织形式的创新,来适应未来的发展。“像我这一轮的组织变革就是为我儿子接班做准备的,我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去打造组织体系,我希望最终交到他手上的是一个符合他要求的组织模式。深思熟虑的接班,可以避免过往接班突发性和偶然性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
面对未来的产业方向,徐家心里也有底。除了之前的主业,华茂会在新材料科创领域和竹制产品的制造上做一些探索,回到家族最初的竹编产品的发源上做一些技术攻坚。同时会深耕美育,在美学教育的课程、论坛、奖项设置上都有一整套计划,这是华茂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徐立勋强调:“我们现在做的计划绝不是心血来潮,都经过了家族很长时间的思考和斟酌。我们投入任何一项事业都不会以年为单位去计算,我们会以代计算,一代人做不完的事业,下一代继续干,这也是家族的共识。”从实业到多方向投资再到艺术和教育,华茂的层层递进的转型结构清晰。
2008年,由华茂教育集团投资、首位中国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主持设计的华茂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董事长徐万茂将自己三十多年来收藏的千余件艺术珍品悉数捐赠。而最新的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也已开馆,这是国内第一座以艺术教育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设计者是葡萄牙著名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是其当前在世界上唯一的“黑色系”建筑作品,馆藏包含提香、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大师的近200件艺术精品。如今在华茂美术馆的北侧不远处,华茂国际教育图书馆跨河而建,与美术馆遥相呼应。这座图书馆由同样获得过“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设计,也是其首个中国项目。
作为企业未来的第三代接班人,综合他对艺术和计算机的学习和兴趣,徐钰程已经参与了若干艺术展的数字化搭建和策展工作,父亲愉快地提到近期艺术家丁乙的展览布展就有儿子的参与。
对于家族企业的未来,徐立勋看得很通透:“企业不可能永远存活,可能有一天华茂也会倒,这是自然规律。华茂倒下之前,能够留给宁波这座城市、这个社会一些什么东西呢?假如华茂不在了,但华茂留下的这些东西还在,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