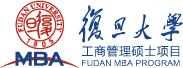影像中的幸福人生
2010年04月27日2010知微·行远论坛第三讲在4月25日如约而至,继孙时进教授告诉我们要营造幸福心灵的港湾、陈思和教授呼吁我们要让生命开出美丽的花朵之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电视艺术家学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吕新雨教授也做客论坛,与同学们一起探讨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幸福观的理解的区别联系,并带领大家从影像中感知幸福,体验幸福。
“幸福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难定义的词”,吕教授开场就说到,没有固定不变的幸福,中国人对幸福的定义也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在古代,“幸福”是一个动词,“幸福而祸,无亦左乎”,我们寻找幸福,可我们却得到了灾难,在那个时候,幸福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而且是一种非常强烈和主观的对幸福的需求和渴望。到了儒释共存的时代,文人学士把“乐”而不是“福”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他们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家国、天下之乐才会幸福。到了革命时代,“幸福观”又发生了变化,无数仁人志士为了理想、为了人类的幸福而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这是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特殊的价值观。再到今天的后革命时代、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又把“爱情”看做是和“幸福”联系最多的词,爱情成了这个时代通往幸福的通道,在世俗意义上又戴带上了乌托邦的意义。
说完了中国人的幸福观,吕教授又对西方的幸福观作了一番回顾。西方的幸福观也是伦理的幸福观,就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善德,是全体公民的快乐,是城邦的幸福。和它对立的是个人主义的幸福观,诞生在亚历山大帝国时代的享乐主义主张人们从宏大的政治叙述中退出来,从战争、暴力、侵略、屠杀中退出来,退到个人的肉体和感官,一切善德、幸福和快乐都回归到自我。而犬儒主义则认为权利、富贵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外在的,都不能取代心灵,因此他们认为幸福应回归到肉体和心灵,第欧根尼的名言“人被打上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破铜烂铁打上了假印戳罢了”就是最好的解释。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来源,可是今天的个人主义却主张追求个人的肉体和欲望的满足,这和古希腊哲学里的早期个人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吕教授说,幸福不是短暂的满足,而是对重复、对永恒的追求。幸福这个词背后有广阔的社会和历史内涵,会作用在每个个体的身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吕教授带领同学们观看了一段关于两位老人的影片,然后和同学们就这段影像进行了一场关于幸福的对话。
有人从“幸”这个字形上说,“幸”上面是一个“土”字,代表房子,下面是一个人民币的符号,代表钱,这样的解读很符合今天这个时代世俗对幸福观的理解:幸福就是有钱有房子,那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幸福就是主观的,还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幸福有没有程度的对比?一个人一直很开心满足是不是就是幸福?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用钱和房子来定义幸福,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这个主流价值观里把自己解放出来,打破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对于幸福观的理解,不然我们就只能成为钱奴和房奴。
吕教授的讲座,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没有告诉同学们一个答案什么是幸福,但是却给了同学们不同的视角,包括中国的视角、西方的视角、历史的视角和现在的视角等去审视幸福的不同。真正的幸福应该从每个人的命运出发去寻找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拥有一种淡然的生死观,在喧闹的环境和繁忙的都市生活中,用精神的力量来获得内心的安宁,并且让这种幸福感扎根到家国和天下,做到尽人事、知天命。在四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同学们又进行了一次对幸福的思考和对心灵的洗涤,而5月8日的知微·行远论坛将邀请到陆悦农先生用文字与摄像机带我们去寻觅幸福的旅程,敬请期待。
MBA项目
2010.4.27